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,落实教育部要求,北语关工委统一部署,由关工委秘书处(离退休工作处)牵头、在宣传部、人文社会科学学部、汉语国际教育学部的大力配合下,组织了对16位“五老”(老干部、老战士、老专家、老教师、老模范)和学生的结对采访,聆听了老师们参加祖国建设的奋斗历程、感人事迹和真实感悟,用文字记录了他们作为实践者和见证者的亲身经历、亲身参与的学校发展的故事。通过访谈感受变化和老师们不忘初心、牢记使命的担当。
人生,活着就是奋斗
——阎纯德老师采访录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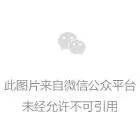
阎纯德老师的人生关键词就四十四个字:“感恩国家!人穷志不穷;人生,活着就是奋斗;做别人想不到或没做过的事,在有生之年贡献自己的绵薄之力……” 阎老师出生于河南滑县,后在最艰苦的1942年,流落到濮阳黄河边。他幼年家贫如洗,身世坎坷,但这并没有阻挡住他对知识的渴望。在国家的支持和自己的奋斗下,阎老师以优异的表现读完了小学、中学,为实现其文学梦,其后又顺利地考上了北大中文系。
回忆起以前的艰苦岁月,他从心底感谢国家。“没有国家的支持,我不可能从东明、开封一路走到北京。这路太长,光靠自己的力量,我走不下来……”阎老师反复说起自己“人穷志不穷,不肯认输”的奋斗性格。他说“作风”是培养的,“性格’是天生的;“像我这样的人,从某种意义上说,时代给我打了太多的烙印,没有国家这份厚爱,我不会有今天……”
阎老师作为国家汉语师资出国教授汉语和文化,在法国前后七年,在巴黎大学和国立巴黎东方语言文化学院四年多,他教过的学生,有的成了知名的汉学家,有的做外交官,也有在欧盟驻中国大使馆任职的。
阎老师从初中开始就喜欢文学。北大中文系毕业后一直到现在都是在从事文学教学与研究,还有创作,除了文学研究的著作,如《作家的足迹》、《瞿秋白》和《二十世纪末的文学论稿》,还有诗集和多部散文集出版,文章还被选到九年制的全国语文教材和中学教材。阎老师说在研究上决心要做别人没有做或没有想到做的事。1977年从巴黎归来后组织和主编中国百年文学史上第一部《中国文学家辞典》。收录了近4000名作家,再有就是对中国女性作家群体的研究。这件事缘于巴黎,在那里他读到庐隐和谢冰莹的作品,他想这么重要的作家,中国当时的各种文学史竟然没有予以正当的评介;当然,这件事也和著名汉学家米歇尔·鲁阿(Michel Loi)夫人的提示有关。回到国内,他采访过许多重要女作家,如冰心、丁玲、谢冰莹、赵清阁、菡子、茹志娟、刘真、柯岩、黄宗英等,出版了《中国现代女作家》(主撰)、《中国女作家小传》(上下卷)、《中国女作家研究》等,还主编了“二十世纪华夏女性文学经典书系”(11卷)等。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,他有了创办《女作家》的杂志的想法,在1983年还请茅盾题写了刊名。当他进入“80后”之时,为了这个半世纪的梦想,终于在学校的支持下将于2020年春由作家出版社出版《女作家学刊》。杂志将以多元的领域,多元的学术视野与观点,成为中国女性文学研究绚丽的天空。阎老师在编辑会上说,“我以'筚路蓝缕,以启山林'之心,在学校这块肥美的土地上为各位打地基,这座楼究竟能盖多高?就靠你们努力不断添砖加瓦、不断加固增高了!我想在我的有生之年能听到春风里的女声大合唱……”
他在1993年创办和主编的《中国文化研究》。这年春,教育部来北语调研,他在会上根据法国教书的经验,建议国家出版一本传播中国文化的杂志。根据学校的安排,于是,他离开了语文系,走上了编刊之路。当年4月接受任务后,便独自一人骑着自行车满城跑,不是教育部,就是新闻出版署。当时,他没有办公室,也没有编辑,一个人在家里编好特大创刊号,并于8月5日正式出版,张岱年、任继愈、季羡林等近二十位大家为它题词并撰稿,并受到读者广泛好评,很快成为“北核”、“南核”的名刊,还被不少大学定位为AAA级杂志。从这个杂志的创刊号开始,SINOLOGY—汉学研究便有了一个名正言顺的平台,登上了中国学术的舞台;翌年,他又创办北京语言文化大学汉学研究所和《汉学研究》,克服种种困难,《汉学研究》坚守至今,并使之成为在国内外影响广泛的CSSCI来源集刊。
办刊物就是为人作嫁,这确实需要一种奉献精神。没有执着坚定的事业心,是办不成的。办刊物没有节假日,不停地处理稿件,给作者回信,指出其稿件是行还是不行,还需要做些什么,是修改,还是压缩,有时还得在网上为作者查对信息。阎老师说自己既然已经钻进了这个胡同,那就得往前走。他并不是无事可做,自己还有七八本书等待出版,有整整撰写了半世纪的百多万字的《百年中国女作家》及《中国女性文学的前世与今生》、《台港澳及海外华文女性文学史稿》也都是他基本写成而尚未出版的书稿。
为了让有着三百多年历史的SINOLOGY焕发光彩,从20世纪末开始,阎老师又筹划“列国汉学史书系”,至今已出版“列国汉学史丛书”和“中国文化经典传播与研究丛书”等六十来部,在海内外都产生了良好影响。
阎老师说,北语对国家的贡献非常大,承担着培养汉学家、传播中华文化和中外文化交流的任务。事实上我们学校已经培养了不少正在各国耕耘的汉学家。这几年,习近平主席不仅提出“人类命运共同体”的构想,还多次提出开拓国际文化交流,支持汉学研究的发展;而我们学校算是先走了一步,是国内学界最早从事研究的大学。阎老师认为北语就像一棵大树,它应该枝繁叶茂,我们学校应该是语言的北语、外语的北语、文化的北语、汉学的北语、文学的北语、艺术的北语!
阎老师今年年底年满80,友人劝休息,但是阎老师依然坚持每天工作六七个小时,回邮件、写信、写日记、写文章,不亦乐乎。今年8月至9月,为了《女作家学刊》创刊所遇到的困难,使他十数日彻夜难眠。
从一个逃荒要饭、被卖被买的苦孩子,一路从黄河滩经过东明和开封,然后又跑到北京和巴黎,阎纯德老师说,“只要我中途不倒下,我就不会停下来,一定要跑过终点线。” 他还说他不会忘记自己的人生关键词!
采访:人文社会科学学部本科生党支部
喻茜 庞镕榕 甘嘉铭 徐璐
文字整理:人文社会科学学部党支部
赵美

